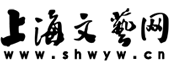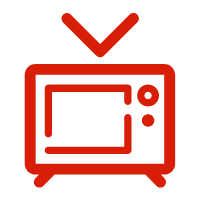“律動的歲月”系列專訪:被歌聲眷顧的人生——孔鴻聲訪著名詞作家施翔

左起:施翔與孔鴻聲
“創作是我的日常,寫歌是我生活的樂趣,記得德國鋼琴家、作曲家羅伯特?舒曼說過:藝術家的職責是用光照亮人類心靈的黑暗之處。我每一次寫歌的瞬間,也都是對自己靈魂的一次次燭照吧,歌聲讓我變得溫暖柔軟,讓我變得豁達開朗,讓我變得心中更有愛,進而也讓我總想用子規啼血的歌聲去呼應這個可歌可泣的時代。回首往昔,盡管履歷豐富,經歷不少,但真正熱愛的事情,一輩子都愿意做下去的好像只有寫歌這件事了,生活給予了我那么多,我只有、也只能以歌報答,歌聲是我留給這個世界最純真的禮物。”
“如果從1988年我和著名詩人顧城同在《光明日報》主辦的賽事上一起獲獎的《日月之戀》算起,那也是我平生寫下的第一首歌詞,至今我已經寫了30多年了,創作歌詞近3500余首,被譜曲灌錄的有500余首,但我仍然沒有停下手中的筆,仍在心無旁騖的研學思考與探索實踐。我為什么在歌詞創作這件事情上能夠長久堅持,因為在攀爬這座‘詞山’的途中,我至今還沒有看到山頂,還沒有看到最美的景色。我以為自己寫得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首,再下一首。”
這就是筆者專程從上海前往杭州,在美麗的浙江財經大學采訪該校公共藝術教育中心藝術顧問、著名詞作家施翔時他的開場白。
其實,無論做任何一件事情,什么是“好”?何時是“頂”?它缺少具體的統一規范或標準,只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蘇浙滬三地,施翔是一位出類拔萃、高產優質的詞作家,其作品的含金量是詞界公認的。為什么他從事歌詞創作30多年還自認為沒有見“好”?還未見“頂”?筆者理解為:這是他一生中最為鐘愛的事情,也是他一生中最愿意花時間認真去做的事情。他甘愿在這座“詞山”上,腳踏實地地去攀登、孜孜不倦地去探索,以詞為憂,以詞為樂。說到底,這就是他這一生中心底里積淀厚重而揮之不去的音樂情結。
施翔,詩人、詞作家、音樂人、文藝策劃撰稿人,出版《一管短笛吹青春》等專著和音樂大碟多種,國際國內獲獎百余個。中國音樂文學學會常務理事,浙江省音樂文學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他曾為許多城市、農村、單位創作過市歌、村歌、校歌、行業歌曲、旅游形象推廣歌曲及電視劇插曲等其它主題歌曲,也為省市許多大型晚會和主題音樂會及電視專題片做過策劃、主創和撰稿人。由其創作的《舞動中國》等歌曲風靡全國,紅遍網絡。《早春的腳步》、《夢想走在大路上》等歌曲多次獲得過文化部“群星獎”、中國音協優秀創作歌曲獎、浙江省“五個一工程獎”、浙江省音樂舞蹈節大獎、浙江省音樂新作大賽大獎、全國村歌大賽大獎等。同時他還經常應邀在各地作有關音樂文學創作的系列講座,作品點評,大賽評委,深受廣大詞曲愛好者的青睞和歡迎。
施翔雖然剛過耳順之年,但他的人生閱歷卻是多姿多彩。在采訪過程中,聽他敘說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其中不乏有感人的歌詞創作回憶。當筆者準備動手撰寫這篇專訪稿時,因可寫的東西實在太多,不知該從何處寫起、怎樣落筆?有點為難了。思考再三,還是說說他近年來已經發行和即將出版的三張歌碟吧!常言道:窺一斑而知全豹。但愿此文能達此意。
情感+詩意化的《西湖煙雨歌》
《西湖煙雨歌》是施翔在2017年推出的一張原創音樂大碟,共有12首歌曲組成,以杭州最為著名的景點作為落筆原由。按碟片排列的秩序分別為:蘇堤春曉、花港觀魚、三潭映月、云棲竹徑、雷峰夕照、柳浪聞鶯、平湖秋月、雙峰插云、南屏晚鐘、斷橋殘雪、曲院風荷、靈隱禪寺。楊昊東、蘭曉飛、張葉帆三位作曲家為之譜曲,作品系杭州市委宣傳部文藝精品工程立項項目,由浙江文藝音像出版社出版發行。
這部組歌最初的取名稱《西湖十景》,是在2013年浙江省音樂家協會舉辦的“美麗浙江”歌曲征集活動中嶄露頭角的。作品除描述形成于南宋時期的老“十景”外,另加上《云棲竹徑》和《靈隱禪寺》2首,后更名為《西湖煙雨歌》。
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筆者用了近2個小時,靜心地聆聽了這12首歌曲。對于一貫喜歡民族音樂的筆者來說,細細地品味這流行而又時尚的曲調,倒也感覺蠻入耳的。只是不敢飲茶,更不敢喝咖啡,怕影響后半夜的睡眠。辜負了作者“是為人們在西湖邊喝下午茶或夜咖啡的時候,可以隨意拿來傾心聆聽或對歲月對過往能夠勾起漫漫回憶”的創作初衷。還好筆者是半躺在床上瞇著雙眼傾聽的,并沒有坐在美麗的西湖邊。
《西湖煙雨歌》一經問世,即刻贏得音樂界的強烈關注,贊揚聲、褒獎聲從四面八方匯涌而來。為什么這組歌曲能得到這么多音樂界大咖、名家的青睞?還是先來聽聽諸家各路對《西湖煙雨歌》是怎么評價的吧:
在大量的作品中,我又一次無法拒絕地發出了羨慕的感嘆:詩人施翔的《西湖十景》(后改正題為《西湖煙雨歌》)以獨有的心靈體驗與詩化的藝術語言,為“淡妝濃抺總相宜”的西湖再次發聲,提供了一部規模可觀的歌詞文本,著實讓人欽敬再三。——北京?著名詞作家、音樂文學評論家晨楓
施翔用高于生活的詩,用精良的音樂制作,表達了西湖山水在他成長路上留下的記憶與印象。組歌不單純寫景,更多抒發和感懷的是心境。音樂的定位統一:以流行化的編曲切入,輔以適當量的中國風元素。雖降低了受眾聽歌的門檻,但讓當下大多數人都能享受其中,這不正是值得推崇的嗎?一一浙江?中國國際動漫節音樂總監蔡近翰
詩與歌詞同源的道理大都能明白,但要處理好并非每個人都能做到。在這方面,施翔不僅做到了,而且做的非常出色。歌詞需要詩的滋養,能讓歌詞像詩一樣更富有情意,而詩同樣需要歌詞的觀照,能讓詩像歌詞一樣飛得更高,飛得更遠。一組《西湖煙雨歌》水到渠成,將西湖美景中的歷史文化,通過個性化的人文體驗,以歌唱的名義進行了詩意的表達。為西湖代言,施翔選擇了一種最美麗的方式。一一上海?著名詞作家、原上海音樂文學學會會長湯昭智
天下以杭州美,杭州以西湖名,西湖以歌賦傳。凡傳世之作,必有獨到之處。細讀《西湖煙雨歌》,亦有其別樣的氣質與獨特的韻味。其意蘊,般配了這一湖煙雨;其情致,契合了這一湖花月。西湖是水做的,水做的風景便在組歌里次第呈現,洇潤了眼眸,暈染了心波;西湖是情砌的,情砌的故事便在組歌里逐一展開,浪漫了幽怨,詩意了愛恨;西湖是大眾的,也是個人的,以個人的感悟對接大眾的體驗,這組歌做得十分巧妙;西湖是歷史的,也是今天的,從今天的視角切近歷史的影像,這組歌亦不乏奇思佳構。一一江蘇?著名詞作家、原南京軍區前線歌舞團創作室主任李峰
就我而言,雖然多次游歷西湖,始終未能下筆,因為有東坡的詩、又有《南屏晚鐘》《千年等一回》《斷橋遺夢》許多大作在前在上,只能像李白一樣喟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故爾,不能不贊施翔之青春才氣與苦吟之志!一一江西?國家一級編劇、著名詞作家、原江西歌舞團團長秦庚云
而國家一級編劇、著名策劃人、撰稿人、詩人及歌詞作家任衛新,在評論《西湖煙雨歌》時,則將它稱為“西湖十二闋”,他認為:蔡文姬有胡笳十八拍,曹雪芹有金陵十二釵,西湖完全應該有資格贏得這樣一個品牌的。
任衛新在評論中寫道:“可以肯定:施翔寫這十二首西湖歌是苦心孤詣著實花了一番功夫的。因為他不花功夫也不行,西湖的名氣在那里擺著,前人的名作在那里擺著呢。……愛西湖這個美女的人太多,各種示愛的招兒都用過,能把這個美女拿下的卻不多。”
“于是,輪到施翔霸王硬上弓了,一下子干了十二首。想方設法尋找各種角度,使盡各種招數,選擇各種情景來強攻,其中不乏勇氣,不乏才氣,也不乏力氣。至于里面那些潛心用思,潛心用意和潛心用詞,咱們就不說它了。總之,讓我們欣喜地看到,他完成了。”
引用了這么多音樂界大咖、名家對《西湖煙雨歌》的贊譽后,對這部組歌在音樂界的影響力如何,無須筆者再多費筆墨了。筆者想說的只是:施翔在創作這部組歌時,并不是就事論事地將它們以景點介紹、景色描繪方式來創作,而是把他自己內心世界對社會、對生活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溫柔地融入進每一首作品中,以詞喻情加以抒發。如他自己所言:“《西湖煙雨歌》只是用西湖實景做了一個創作的背景而已,主要還是想通過對眼見的風景來幻化成自己內心最想傳達的意趣和情愫。說真的,跑遍了整個世界,對生我養我的杭州,我終究是愛戀有加、情有獨鐘。”
美感+正能量的《最美杭州》
2016年7月,杭州有一則新聞引得國人關注,筆者簡摘如下:施翔、丁震華、陸琦、陽一,這四個從60后到80后的杭州男人,最近干了件了不起的事。今年5月27日,這四個男人一起創作了一首歌,7月25日,99個杭州市民齊心協力零報酬出演,將這首歌拍成了MV,上傳網絡。如今,這首歌的MV點擊量已經破千萬,成了網紅歌曲。歌的名字,叫《最美杭州》。
“把鑰匙交給你,陽臺上望天,白云掉進錢塘,星星在西湖洗臉。”“最美杭州,請你來到我身邊,愛在山水間,依偎過就留念;最美杭州,是天堂更是人間,西子好姑娘,就等你來相牽。”施翔回憶道:“當《最美杭州》的曲作者陸琦在晚上9點多鐘向我發出邀約后,第二天一早,一首朗朗上口的歌詞就交稿了。我是凌晨3點一覺睡醒起來寫詞的,在寫作前,腦海里小時候的杭州和現在的杭州交疊出現。小時候我翻過西湖邊的城隍山去杭四中上學,走在青石板路鋪滿的大井巷里,而現在的大杭州已是車水馬龍,霓虹閃爍,徹夜不眠,內心滿滿的是對杭州的自豪和驕傲,迫不及待地想和所有人分享。只用了15分鐘,歌詞就寫出來了。”
原來,2016年9月,G20峰會將在杭州召開。這四個杭州男人,希望依托舉世矚目的G20峰會召開為最佳鍥機,做一項有意義的公益活動,宣傳推廣中國、宣傳推廣杭州,在世人面前充分展示人間天堂的秀美山水和人文風貌。他們最終如愿了!《最美杭州》唱出了所有杭州人的心聲和幸福感。
兩年之后,施翔以《最美杭州》一歌作為主打歌,另選取了13首歌曲,又組成了一張原創歌曲大碟——《最美杭州》,作為向新中國成立70周年以及2022年將在杭州舉行的亞運會的獻禮之作。這張大碟所收錄的14首歌曲,主要表現兩大塊內容:一是為各類晚會所寫的主題歌。如“杭州市第六屆西湖博覽會會歌及閉幕式主題歌”的《再約杭州》、“中國南宋文化節”的《宋韻小唱》以及“中國南宋文化節專場文藝晚會”的《風雅頌天城》等;二是為一些古鎮和景區所創作的形象宣傳推廣歌曲。如杭州市靈隱地區的《愛到無語》、杭州市余杭區南山景區的《南山上》、杭州市塘棲古鎮的《塘棲印象》、杭州市轉塘畫外桐塢的《畫外桐塢》等。這些作品看起來好像都是一些應節應景之作,但當你細細品讀時,可以強烈地感覺到施翔是借應節應景創作之際,以他滿腔的赤子之心體現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的使命擔當,同時也是在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的藝術創作中實現著自己的音樂夢想。
浙江是一處步步山清水秀、回望景色迷人的地方,真如眾多游客所贊:隨意拍攝一張照片,就是一幅姹紫嫣紅的圖畫。浙江的城鎮水鄉特色各異,有古遠的歷史遺跡、有厚重的文化積淀;有美麗動情的故事,有撲朔迷離的傳說……。施翔說,為了創作,他走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至今已應邀寫了一百多首各地的形象推廣歌曲及村歌,其中有不少單曲在省級及以上的全國大賽上獲獎。
施翔給筆者講了這樣一件事:杭州有個美麗的鄉鎮,管轄有19個自然村,該鎮要搞個“村村有歌聲”的比賽,邀請他為他們寫“村歌”。當時對該鎮有特色的村莊他都寫了,最后留有一些只有共性而無特色的村莊沒寫。鎮領導希望他繼續把這些村莊的歌寫完,他說他實在寫不出來了,但他會推薦其他的歌詞作家來寫,也許在他們的眼里能發現這些村莊的獨特之處。
施翔對筆者坦誠:“其實為那些沒有特色和個性的村莊寫首歌我也寫得出來,或許也會寫的不錯,稿酬我也照樣能拿。但我覺得沒有靈感的激發,沒有新意的跳躍,這樣的寫作只能是在重復自己過去的創作。這種讀起來使自己都會感到索然無味的作品,拿了稿費后我心里會感覺很不舒坦。所以,對邀約方,如我覺得要寫的東西對我沒有產生濃厚的創作興趣和激情,沒有我感到需要深思創作的價值和意義的所在,在情感上缺乏創作的共識共鳴和挑戰性,就是給我再高的稿費,我都會婉言謝絕的。”
歌碟《最美杭州》,雖然是以“施翔原創歌曲作品選”名義問世,但從它的創作和發行方來說,其實還是政府在做這件事。除主打歌是施翔與伙伴們自發創作外,其他13首歌曲,都是有杭州市政府相關部門或杭州市所轄的地方政府委托施翔所寫,最終又以“杭州市文化精品工程扶持項目”出版,由浙江文藝音像出版社出版發行,從歌曲所表達和頌揚的內容上,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張充滿了正能量,又頗具個性風格和魅力的歌碟。
對于主旋律的歌詞怎么寫,特別是如何寫好政府部門邀約的主題曲作品,確實值得詞作家們深思一番。筆者曾經聽好友說起過這樣一件事:某級政府委托他創作一首頌揚主旋律的歌詞,歌詞寫出后送領導審閱,領導們總感覺“正能量”不夠,于是層層審閱,層層修改,結果把原作者的歌詞只改剩保留下一個“啊”字。最終這首修改后問世的作品確實充滿了正能量,其語句和詞組的內容,完全就成為領導臺上所作報告的“歌詞版”。這樣的歌曲能唱嗎?當然能唱!但它缺少音樂作品應有的藝術感染力。
而施翔在寫類似作品時,他的創作理念是:“要我寫,我就要寫成我想要的東西,但我也會充分考慮到邀約方的需求。我會把自己對創作的認知和審美盡力融化在邀約方所想要的需求里,盡可能地說服邀約方使歌曲的立意和語言靠近藝術而遠離概念和口號,使雙方盡可能地達成共識。在創作上,我始終想把自己的個性感受融入到社會這個大格局里去,因為唯有如此,我的格局才能變得越來越大,在時代的大格局里有我的小世界,而在我的小世界里,也能盡情體現出波瀾壯闊的大世界,這就是我對創作主旋律作品的領悟。這樣寫出來的作品,既滿足了自己創作的愉悅感,同時也會贏得受眾的親和力,我想只有將自己真正融入到生活中去,并始終懷抱家國情懷、赤子之心,寫出來的主旋律歌曲才會是動聽的,才會受到老百姓的歡迎和喜愛。
筆者認為:施翔對主旋律作品的這一創作領悟和方法,是值得借鑒的。而歌碟《最美杭州》就實證了這一點!
動感+年輕化的《海的印記》
施翔在他的筆記里寫道:如果說山是地球的父親,那么海便是地球的母親。施翔新近創作的《海的印記》,就是他唱給大海母親的一組深沉摯愛的歌。一部以大海為主題的音詩畫歌舞秀劇本《海的印記》,共有10首歌曲和4段現代舞組成,即將作為浙江省某濱海城市新建的大劇院落成獻禮劇目隆重推出,其全劇演出的策劃文案也是有施翔自己設計撰寫的,這也是施翔目前正在忙碌著要出版發行的一張新歌碟。施翔創作這部《海的印記》的初心是:試圖通過散文式、碎片式的獨白和歌吟,表達出人類對大海所珍藏的美好記憶以及典藏的熱愛,更期待通過體驗式和會心化的現代音樂語言的傳遞,匯聚成一部有關大海、地球、生命,愛與不舍的靈魂之歌。
《海的印記》通劇呈現的是一股蓬勃向上的氛圍,形同大海翻滾不息充滿活力和壯麗之美。施翔說:“《海的印記》表達的是我對美好青春的回憶,記錄的是我對已逝歲月的懷念,所詠嘆的是我的人生的理想之歌。”
《海的印記》之所以給人的印象是青春的、動感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它的音樂能讓人聽之舞動、跳躍起來,體現出大海不安分的性格。這也難怪,因為《海的印記》的曲作者就是一位剛過而立之年、正青春難遮的年輕人。
想想也讓人覺得有些“傳奇”,一位是已過花甲之年的“爺爺輩”,一位是剛越過當立之年門檻的小伙子,倆人年齡懸殊一倍,卻能相擁共同的創作靈感走到一起,奉獻出一部令人看好的大劇。經詢問,這里確有一段“傳奇”的故事。
作曲者戚超馳,原來是工作在溫州永昆劇團的一位音控師,他無意中在北京的《詞刊》上(2015年第1期)讀到了施翔《秋天的海邊》一詞,很是喜歡并為之譜了曲,并準備推送參賽,但不認識詞作者,后在劇團團長的牽線下聯系上了施翔。施翔聽了小戚為《秋天的海邊》所譜的曲調后,非常欣賞,覺得這位年青人很有作曲天賦。果不其然,2020年在人民音樂家施光南的家鄉——浙江省金華市舉辦的“首屆長三角原創流行歌曲大賽”上,《秋天的海邊》榮獲了大賽的創作金獎。接下來,施翔毫不猶豫地將《海的印記》中另外9首歌詞全部給了戚超馳,并鼓勵他大膽地去創作,就這樣一部一老一少音樂人心靈之約的“音詩畫歌舞秀”在冥冥之中的緣分安排下驚喜地誕生了。
其實,施翔能與戚超馳合作成功《海的印記》,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施翔人雖年齡漸長,但卻仍然擁有一顆年輕的心,身上還驛動著一股年輕人所具有的青春活力,這在他近年來所創作的歌詞越來越受到年輕作曲家的喜愛而得到佐證。
施翔告訴筆者:“在多年之前,女兒對我的歌曲創作不甚滿意,她認為詞曲都太墨守成規了,跟不上時代的節奏,年輕人不喜歡,套路就是死路。聽到女兒直率的批評,我當時蠻失落的,寫了一輩子的歌,卻得不到年輕人的認可。后來想想女兒的話也是有道理的,作為搞流行歌曲評論的年輕人,她的觀點代表了當今時代的一種潮流、一種趨勢、一種追求。自己的歌詞創作確實需要‘年輕化’了,需要不斷的學習和創新,才能贏得聽眾,否則被社會淘汰就是早晚的事。”
“近年來女兒對我和團隊創作的歌曲越來越喜歡了,她說老爸你年紀越來越老,作品卻寫得越來越‘年輕’了,越來越與這個時代接軌,越來越能融入現代生活了。從女兒的話語中,我認識到自己的創作理念、創作走向、創作心態、創作風格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轉變,變得與當今社會越來越靠近了。”
說到創作的“年輕化”,施翔的童心更是生生發了芽。已做外公的他,接下來準備將歌詞創作的方向朝兒童歌曲板塊轉移,他說他老了要讓自己像小孩子一樣,活得更簡單一些、活得更有趣一些,活得更純粹一些。“
由此可見,施翔在歌詞創作上所呈現的“返老還青”、“返老還童”現象,并不是他一時的心血來潮之舉,只能理解為他在“詞山”上的奮力攀登,確實還沒有見到“山頂”,所以他還不能、也不會停下腳步。“那怕活到80歲,只要還能寫,我一定還會快樂地寫下去,寫歌永遠是我前行的動力和希望!”一語所表,這就是施翔心中那份揮之不去的音樂情結。
施翔,被歌聲眷顧的人生是幸福的!
采訪于2021年6月16日
責任編輯:沈彤 楊博
新聞熱線:021-6131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