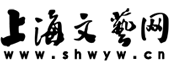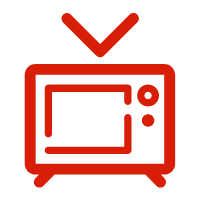牛年新春前的一個午后,跟京劇名家尚長榮和知名導演滕俊杰相約,在衡山路上某處喝茶。剛落座,滕導便透露一個“秘密”:“尚長榮先生有個幸運數字:三。”
細數起來,尚長榮有一個姐姐兩個哥哥,三兄弟中行三,幼時長輩們都叫他“老三”;
尚長榮、高立驪夫婦育有三個兒子;
他一生在三個城市工作生活過:北京、西安和上海;
他最為人稱道的是三部新編歷史劇《曹操與楊修》《貞觀盛事》《廉吏于成龍》;
他三次參加中國京劇藝術節,三次位列金獎榜首;他三獲“白玉蘭獎”,三得“梅花獎”,是第一位梅花大獎獲得者;
他和滕俊杰合作了三部3D全景聲京劇電影《霸王別姬》《曹操與楊修》《貞觀盛事》,全部獲“金雞獎”最佳戲劇電影提名,《貞觀盛事》最終獲獎;
應邀到海外推廣這三部電影,他三赴美國、三赴歐洲、三赴日本……
說到這里
我說尚老師還有一個“三”
只是要在后面加個“十”
從1991年正式從西安調入上海京劇院算起
今年是他“入籍”上海三十年
尚長榮出身于梨園世家,父親是京劇大師尚小云。他五歲登臺,在《四郎探母》中演楊宗保。父親擔心他上臺后害怕往回跑,特意加了四個“大鎧”,他個頭只到他們的腰部,一上場臺下掌聲笑聲一片。“大帳”一場中,楊宗保要落座,但椅子太高,只能由撿場師傅抱他上去,臺下又是一陣掌聲笑聲。
但父親當時的考慮,還是想讓老三上學。直到尚長榮十歲那年,老師姐吳素秋對尚小云說,大弟、二弟在舞臺上很有成就,為什么不讓三弟長榮學戲呢,現在花臉很缺,不如讓三弟學花臉。由此,尚長榮正式拜師學花臉,至今已經整整七十年。
“我后來見到老師姐就說,幸虧您建議我學花臉。如果學老生我肯定不像,如果繼承我父親,就是八個字‘不堪入目,慘不忍睹’。還好學了花臉,直到現在‘80后’了,還能上舞臺。”尚長榮半開玩笑地說。
七十年花臉生涯中,有三十年是在上海度過的。而在“入籍”上海之前,他就夾著《曹操與楊修》的劇本,“潛入”上海灘,尋求與上海京劇院的合作。他發現,上海這個城市一點都不排外,沒有門戶之見,自己在上海可謂如魚得水。因為《曹操與楊修》的大獲成功,也因為上海市領導的多次誠摯邀請,讓他萌生了加盟上海京劇院的念頭。雖調動過程有點波折,但1991年終于得償所愿。
對于“入籍”上海的這三十年,尚長榮感慨有加。他在這個城市,連續創排三部新編歷史劇,對京劇藝術如何“守正創新”,有了深層次的研究與實踐。而這個城市,也讓他最終登上了藝術巔峰。
“我的好朋友,曾經擔任上海京劇院院長的黎中城對我說,長榮兄,我們把你看準了,你把我們看透了!”尚長榮如是說。
尚長榮:1940年7月生于北京,京劇花臉表演藝術家,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京劇)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兩次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章。曾任中國戲劇家協會第五屆副主席,第六屆、第七屆主席,現為中國文聯榮譽委員、中國劇協名譽主席。
第一章 潛入
高淵:您跟上海的緣分要從什么時候說起?
尚長榮:我出生在藝術家庭,父親和兩個哥哥經常練功排戲,我父親還創辦了“榮春社”,陸續招了幾百名學生。所以我從一出生,就泡在了“戲罐子”里。
我小時候長得虎頭虎腦,小名叫“大福”,教員和學員們都喜歡逗逗我。有一天我在家里,聽到“榮春社”頭科一位叫徐榮奎的老生學員的一句叫板,聲音十分洪亮,把我嚇了一跳。回過神來,被他的唱念給迷住了,就纏著他教我。于是,我學會的第一句京劇念白,就是徐師哥教的“將軍,慢走”。這出自上海周信芳先生的麒派名劇《蕭何月下追韓信》,那年我不到五歲。
高淵:您的第一聲京劇就學了“海派”,父親聽到后是什么反應?
尚長榮:我學會了“將軍,慢走”后,成天在家里每個角落喊,很快被我父親聽到了,他對家里人說:“好啊,看來這個‘老疙瘩’也能吃唱戲這碗飯了。”
高淵:頭一回來上海演出是哪一年?
尚長榮:是1951年5月,那年我11歲,這是我第一次來上海。那次是在天蟾舞臺,跟我父親和兄長們一起演出《遇皇后》和《御果園》,《遇皇后》我演包拯,《御果園》我演尉遲恭。我記得當時的天蟾舞臺的觀眾席有三層,3500個座位,舞臺底下有個很大的化妝室。臺板是用很寬很長的好木材拼接而成,不僅平坦,而且有彈性,非常適合京劇演出。
當時登臺感受最深的是這劇場真大,聽說是東南亞最大最好的劇場,而且全場客滿,觀眾們特別熱情。我上場前,一旁的趙桐珊先生(藝名芙蓉草)對我說:“老三,這可不比北京,上去觀眾要叫好,你可別讓觀眾的叫好聲給嚇回去。”果然,我一上場真的從三樓傳來巨聲叫好,就像一道炸雷劈了下來,著實震撼到了我。
高淵:除了那聲炸雷般的叫好,那次上海之行還有什么讓您印象深刻?
尚長榮:我父親上一次來上海演出是1937年,在黃金大戲院連演一個月,后來因為抗戰爆發,匆匆返回北京,已經14年沒來上海了。
在這次演出間隙,他帶著我們兄弟仨來到黃金大戲院對面一個叫鈞培里的弄堂,在一個小樓前按響門鈴,走出一個瘦老頭,帶著我們走進客廳。我們剛坐下,里面走出一個胖胖的老頭,跟父親抱拳致意,他說知道我父親來了上海,很想前去拜訪,倒讓尚先生親自跑一趟,有些過意不去。
父親讓我們稱他為“黃先生”,每人喝了一碗冰鎮綠豆湯。出門后才知道,那位“黃先生”叫黃金榮,當時我還小,也沒覺得有多大驚訝,但上海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高淵:后來多次到上海演出,對這座城市有什么新的認識?
尚長榮:1955年和1956年我又來上海演出,記得天蟾的硬件設施在逐步升級,那時候已經有“吊麥”了。印象最深的是1983年,那次我同陜西京劇團來演出,我演的劇目是傳統戲《黑旋風李逵》《將相和》和新編歷史劇《射虎口》,頭出“打炮戲”是我和孫鈞卿先生的《將相和》,就有上海戲迷問我:“你為什么不拿《射虎口》打炮?”
這時我才意識到,上海觀眾喜歡新鮮事物,相比傳統老戲,他們對根據小說《李自成》改編的新戲《射虎口》更有興趣。就在那次演出中,我領略到了上海觀眾的欣賞品位和這座城市的藝術氛圍,也認識到我心中的京劇創新意識,可能只有在上海才能得到真正的回應。
高淵: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當您拿到《曹操與楊修》劇本后,決定要來跟上海京劇院合作?
尚長榮:對,我記得是1987年,我的好朋友史美強看到湖南劇作家陳亞先的劇本《曹操與楊修》,覺得適合我演,就推薦給我。我看了之后特別興奮,大有久旱逢甘霖的感覺,仿佛這出戲中的曹操就是為我量身打造的。
跟陳亞先達成合作意向后,我就要考慮項目上馬和人員整合了。那年上半年,陜西京劇團只演了三四場戲,而且上座率不高,那里是秦腔的勢力范圍,京劇氛圍向來不濃厚,不具備創排新編歷史劇的條件。而北京重視的是傳統京劇,相對比較保守。
我想來想去,只有去上海。當時我在上海沒有親戚,朋友也很少,但我感受過上海的風氣,這部劇能否成功不知道,但一定要去上海闖一闖。于是就夾著劇本,坐著綠皮火車,聽著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夜出潼關,潛入上海灘。
高淵:上海對您的態度如何?
尚長榮:我先聯系了在上海的兩位朋友,一位是戲劇理論家王家熙,動身前給他寫了封信,但沒提《曹操與楊修》。他沒回信,而是直接給我發了封電報,表示非常歡迎我去上海。
另一位是上海京劇院的老旦名家王夢云,我跟她有過多次合作。到上海當晚,王夢云有演出,她請我到人民大舞臺的后臺化妝室見面。我帶上劇本,把我的想法和盤托出,她很高興地說:“長榮,你可以啊,我就知道你這次來肯定有事兒。”然后她說,你來得正是時候,上海京劇院新一屆領導班子剛調整到位,正想干一番事業,尤其重視新劇目,但就是沒有合適滿意的本子。
第二天,在王夢云的引薦下,我來到上海京劇院,見到了院長馬博敏、副院長黎中城和孔小石。我開門見山說明來意,并把劇本交給了馬博敏。只過了一天,也就是我到上海的第三天,馬博敏約我到辦公室,告訴我經院領導班子研究決定,《曹操與楊修》一劇可以上馬。當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速度也太快了。
高淵:正式進入排戲階段后,你感覺上海對您排外嗎?
尚長榮:上海是不排外的,而且上海不忽悠人,也不被人忽悠。上海是干實事的,是能干成事的,是能干成大事的,只要志同道合,你有真本事就行。
這部劇排了大半年,1988年上海的夏天格外熱,排練場在京劇院二樓倉庫旁的一個房間,沒有空調,只有幾臺小電扇,排練時汗水流個不停。我住的宿舍雖然有一臺電扇,但吹出的依然是熱風,開窗通風蚊子又會進來。因此,晚上休息時就陷入“蚊帳放下來悶死,蚊帳打開來叮死”的境地。我當時編了一首順口溜:“熱浪襲人,汗流滿面。屋似烘箱,心煩意亂。求索藝術,忍苦實干。功成之日,體重減半。”
高淵:大半年的排練,您是一直住在上海嗎?
尚長榮:因為我的工作單位和家都在西安,我得來回跑。一開始,我把從上海到西安叫作“回西安”,后來在上海待的日子久了,慢慢把從西安到上海叫作“回上海”。
后來算算,大半年里我至少“九下江南”。那時候,西安和上海之間只有一趟直達列車,單程要一天一夜,而且不進市區,終點站是在真如鎮的上海西站。有一次火車嚴重晚點,應該是傍晚五六點到,那次到上海西站將近凌晨2點。上海京劇院派來的車沒接到我,公交車早就停了,更沒出租車。那時候也沒手機,就單位有一兩臺電話,一下班就找不到人了。
我想找個旅館過一夜,但繞了幾圈,竟然找不到一個稍微像樣一點的旅館,只看到有一個人防工事改造的地下室,上面掛個牌子“站前旅館”。走下去一看,這哪里是什么旅館,就是一個地下大通鋪,里面已經住了不少人。但不住那兒能住哪兒,總不能大半夜走著去市區。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背起行囊,坐上了開往市區的公交頭班車,直奔上海京劇院排練廳。根據導演馬科的要求,我們每次排練前都要先做小品,那天我主動要求第一個做,題目就叫“誤點”。演完后,掌聲笑聲一片,我說這就是我昨晚的經歷,大家都倍感驚訝。
高淵:您這是名副其實的“潛入上海”了。經過漫長而艱辛的排練,您覺得《曹操與楊修》究竟與眾不同的關鍵點在哪里?
尚長榮:在人物塑造上,我力求展現一個全新的曹操形象。曹操在傳統戲中是個陰險狡詐的奸雄,臉譜是純粹的“大白臉”,后來在《蔡文姬》《官渡之戰》中,有過一次創新,但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揉了個“大紅臉”,當正面人物進行歌頌。
我覺得這兩樣都不行。我師父侯喜瑞先生是著名的“活曹操”,從他的言傳身教中,我對曹操的人物體會是,他是個有文才武略的文化人,他的奸詐中有點兒瀟灑,有點兒氣質。我決定從人性出發,力圖創造一個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曹操形象。
在臉譜上,把原來的冷白變成了暖白,炭條眉改成了劍眉,三角眼改成長圓眼窩。原來唇上的痣似乎有貶低丑化的意思,我就把它挪到眉上變成一顆朱砂痣,很濃的印堂紅。通過面部臉譜的微調,使曹操的形象與劇中人物越來越接近。此外,曹操的幾種笑,包括怒笑、冷笑、陰笑、開懷大笑,也是我重點揣摩的部分。我在排練時,外面有人聽到各種笑聲,都笑著說:“這不是上海京劇院,而是上海瘋人院。”
當然,更重要的是這部戲的思想深度,它對怎么對待知識和人才有深入思考,對人性深處隱藏的東西,有了精彩而傳神的演繹。這不是在簡單頌揚或鞭笞,而是在真正地思考與分析,觸及了人的靈魂,才能打動觀眾。
高淵:這出戲一炮而紅,出乎您的意料嗎?
尚長榮:應該說,主觀上我有成功的自信,當時我也沒有退路,就是要干。
1988年底,文化部舉辦全國京劇院團會演,可能也是看到了京劇藝術墨守成規的問題,那些年老戲老演、老演老戲,此風甚盛。全國20個院團齊聚天津,每個院團拿出三臺戲,一臺新編歷史劇,一臺近現代戲,一臺經過改編整理的傳統戲,這叫“三并舉”。
上海京劇院拿出的三臺戲是,新編歷史劇《曹操與楊修》、近代戲《潘月樵傳奇》,還有一臺三個折子戲改編的傳統戲。演下來,一個國家級京劇院三臺戲獲6個獎,上海京劇院三臺戲獲18個獎。
第二章:調入
高淵:正是《曹操與楊修》的一炮而紅,讓您萌生了“入籍”上海的念頭?
尚長榮:這出戲當時確實一石激起千層浪,給人以驚艷之感。我跟上海京劇院的合作非常愉快,上京既有豐厚的傳統,又有開拓精神,而且上海有很好的京劇文化氛圍和演出市場。當時我50歲,不想頤養天年,還想做事、要做事,想做大事、要做大事。
梨園行有句老話,叫作“搭班如投胎”。但要想從陜西調入上海,又談何容易。馬科導演說過:“跟長榮合作是成功的,可是我又不敢奢望能把他調到上海京劇院來。”我一直說我不是時代的寵兒,我是個幸運兒。就在我渴望來上海時,上海也向我敞開了胸懷。
有一次,在《曹操與楊修》在上海美琪大戲院的演出結束后,當時上海市委書記朱镕基上臺跟演員握手。他握著我的手說:“長榮同志,歡迎你到上海來。”這雖然不是正式邀請,但出自市委書記之口,我聽出了上海方面的誠意。
高淵:這讓您下定決心來上海?
尚長榮:真正讓我下決心的,是1989年10月的一次座談會。那次是朱镕基會見參加第二屆中國藝術節歸來的上海院團相關人員,我以“客座演員”的身份出席,被安排在第三個發言。我說《曹操與楊修》的成功,應當歸功于上海良好的大環境,以及上海京劇院有見識的領導和志同道合的同行,我在上海的排練和演出工作很愉快。這時,朱镕基插話說:“長榮同志,歡迎你到上海來工作。”
根據我的理解,這是一次鄭重的邀請。當時聽了倍感親切和溫暖,我幾乎不假思索地接茬道:“我現在好像已經加入‘上海籍’了!”會場上響起了笑聲和掌聲,似乎大家都歡迎我來上海。
高淵:后來的調動總體還順利嗎?
尚長榮:從正式提出到調動成功,用了8個月時間。1990年,我分別給上海和陜西的相關領導寫了信。上海的信,我直接寫給市委書記朱镕基和市委副書記陳至立,表示愿意接受上海的邀請,我說打算在退休前,實現“八個戲”計劃:三臺類似《曹操與楊修》的重點劇目,五本精排傳統戲。
在給陜西省文化廳的請調報告中,我說我是1959年從北京調到陜西的,已經整整31年,老首長、老領導的諄諄教導和親切關懷,戰友們的親如兄弟之情,三秦父老的哺育之恩,我怎能忘卻,但為了事業大局的需要,卻又不得不割舍這難舍之情。
這之后,上海兩次去商調,但陜西方面始終沒松口。等得久了,我給省委書記和省長寫信,我說八大軍區司令都可以互相調動,我一個戲曲演員,為何調動這么難?到1991年春節放假的最后一天,省長和文化廳廳長來我家慰問。第二天,我接到文化廳廳長的電話,說省委常委會討論后決定放人。
高淵:當時是否也有些朋友勸您留在西安?
尚長榮:有一個好朋友提醒過我,他說長榮,你還是要想想牌子、票子、房子和車子。牌子就是在京劇院團的地位,當時上海京劇院還有好幾位名家,我來了肯定要排在他們后面;票子就是指收入,當時上京的待遇跟全國其他院團比不算高;房子更是上海所短缺的,而我在西安住著大房子;車子我在西安有專車,上海當然不一定有。
我說,我來上海“四不提”,這四樣我一樣都不提。不僅因為我知道上海不會虧待我,更重要的是我來上海不是為這“四子”,我是想為京劇爭口氣,不能為了什么牌子搞內耗。
高淵:“四不提”之外,您提了什么?
尚長榮:我只提戲。1998年,我這個“外來戶”,被評為上海“藝術之星”。在慶功會上,有領導提到明年是國慶50周年,動員大家排大戲。輪到我發言時,我說我準備提倡一個戲,推薦一個戲,期盼排一個戲。然后,我講了我的“魏征夢”,這是我十幾年前就想搞的一個題材,但一直沒搞成,希望能成為國慶獻禮劇。這時候,大家向我投來期待的目光,我說就是李世民和魏征的故事。
其實,對于這個我提倡、推薦、期盼的戲,我并沒有志在必得,因為上馬新戲是一個系統工程,不是想干就能干的。沒想到市領導當場拍板:“這個題材好!”我心想,這就是上海,上上下下都懂戲,尊重藝術規律,也有拍板的決心。
高淵:相比《曹操與楊修》,這部《貞觀盛事》的創新點在哪里?
尚長榮:在藝術上,我求新求變,但不會過分標新立異。有人曾鼓動我演李世民,因為他有突厥基因,可以讓花臉來演,這樣比老生演顯得更新奇。但我沒有接受,因為我還是要考慮觀眾和行家的欣賞習慣。
而對魏征這個角色,也有人支持老生演,因為這是個大文人。但一出戲里不可能兩個主角都是同一行當,我以花臉演知識分子,是極具挑戰性的。
我理解的魏征是個思想家,既剛且柔、敢言善諫,有脆弱的一面,更有脖子硬的一面。為了揭示他的思想,為他設計了大量念白,這在其他戲里是很少見的,它不是敘事性的念白,而是陳述思想。
這部《貞觀盛事》,讓我繼《將相和》《霸王別姬》和《曹操與楊修》之后,第三次獲得中國戲劇梅花獎。按照梅花獎的規則,第三次得獎就是一個梅花大獎,我就成了第一個梅花大獎獲得者。
高淵:“三度梅”時,您已近退休年齡,當時是否考慮歇一歇了?
尚長榮:我喜歡說,我最好的戲在下一出。但當時已經60歲了,我想著把舞臺讓給年輕人,自己多做些藝術總結和傳承工作。但就在2001年,電視連續劇《一代廉吏于成龍》播映,已經退休的《解報日報》資深攝影記者陳瑩看了后,情緒激動地給我打電話,說很適合改編為京劇。
那時候,我的心態跟十多年前排《曹操與楊修》時不同,當年等米下鍋,內心充滿焦慮,這時我已做好退的準備,對陳瑩的建議有些猶豫。她堅持認為只有我能演好,一天幾個電話勸我出馬,還動員袁雪芬等老藝術家來當說客。
我實在架不住這么強大的攻勢,就答應先看看資料。結果就像當年被曹操這個人物所吸引那樣,我的心一下子被于成龍打動了。這時候,黎中城等幾位劇作家也已被陳瑩說動,開始著手京劇改編。
高淵:《廉吏于成龍》是一部典型的好人戲,容易演得“高大全”,而且不像《曹》劇和《貞》劇那樣,有大量的對手戲,這樣的戲不好演吧?
尚長榮:確實如此。我一直認為,創排新編歷史劇,不了解歷史人物是不行的。我專門去了于成龍的家鄉山西呂梁的方山縣,臨走還帶回一抔泥土。后來演出時,這抔土就放在舞臺上象征于成龍廉正操守的竹箱里,我說這是“鎮戲之寶”。
我還在妝上改,決定俊扮花臉,就是不勾臉、不戴髯口,而且不穿厚底靴,也沒有水袖。我在家里拍了一些照片發給導演謝平安,他很驚喜,說這就是于成龍。這樣一來,這個角色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架子花臉,既要有花臉的剛毅,也要有老生的儒雅,還要有丑角的機智。換句話說,要遵循京劇固有的程式,但要活用程式。
我演的于成龍不是偉人,形象不高大,總是頭戴草帽、口叼旱煙袋,有時木訥、有時狡黠,是個近乎老農的普通人。“好人戲”要演好,關鍵是不喊口號,不說豪言壯語,靠的是以情動人、平中見奇。這個戲我演了百多場,先后獲得“五個一”工程獎、十大國家精品劇目、京劇藝術節金獎等,可以說能拿的獎都拿了。
第三章:深入
高淵:您從小學的都是傳統戲,什么時候開始接觸到新編劇?
尚長榮:我是十歲正式拜師學戲,那是1950年,全國大多數地方已經解放了。那時候,文化部有個戲曲改進局,推進傳統戲曲的改革。當時主要是“三改”:改戲、改制、改人。京劇還好,但別的劇種有很多戲是黃色的、恐怖的、暴力的,改戲就是要凈化舞臺;新中國成立前很多劇團都是私人的,受封建把頭的控制,這種制度當然應該改;有很多藝人有不良嗜好,政府強制戒毒、治療性病,這就是改人。
在我的印象中,很多京劇老藝人對此是由衷地擁護。我父親更是身體力行,在1949年11月,他的新編歷史劇《墨黛》就問世了。這部戲改編自他上世紀30年代創排的《北國佳人》。老戲主要表現蒙古上層的忠奸之爭,側重于女主人公小玉報家仇。而新戲偏向于對自由婚姻的維護,更強調下層貧民對惡勢力的反抗。可以看出,我父親是以實際行動表達對新文藝政策的支持。
高淵:您后來演過不少新編現代戲,對那個歷史階段出現的京劇改革,您怎么看?
尚長榮:我第一次接觸現代戲是1958年,當時北京的文化主管部門要求所有的劇團能排現代戲的排現代戲,不能排的在演出前面要加一個活報劇。我第一次演現代戲《不死的王孝和》,跟上海很有關系,我演的是國民黨的憲兵隊長,這也是我第一次演反面人物。后來又陸續創排了《延安軍民》《青楊寨》《平江晨曦》等。
“文革”一開始,我家全家受到很大沖擊,不讓我上臺了。我只能干些拉大幕之類的雜活,幾乎劇團所有的活我都干過,當時是對我的懲罰,其實現在看看也不盡然。比如后來排戲的時候,追光追得不好,我就告訴他們應該怎么追,因為我以前追過,而且我追的時候設備遠沒有現在的好。
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要一分為二地看。比如那些新編現代戲,至少那個時候提出了一個新課題,就是傳統京劇要有新的氣象,不但要演新編歷史劇,還要表現革命題材和工農群眾,這都是新的任務和課題,也進行了一些探索。
高淵:去年10月份,習近平總書記在給包括您在內的中國戲曲學院師生回信中說,戲曲要堅持守正創新。對此,您怎么理解?
尚長榮:總書記的回信情真意切,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戲曲事業的高度重視。我從事戲曲工作七十多年了,至今仍覺得這是寶藏,從根上說,這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藝術的魅力。它的程式、語言和旋律,遵循的美學原則和精神內核,代表著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
但是傳統并非不創新,古典也并非不時尚。回顧戲曲藝術的道路,本身也是在包容創新、兼收并蓄中發展演變,比如京劇能夠集各劇種的優點,使之融會貫通,節奏明快,旋律順暢。我在上海這么多年,創排了《曹操與楊修》等三部新編歷史劇,所遵循的原則從未改變,那就是不僅要尊重傳統、研究傳統、繼承傳統,還要激活傳統。這三部曲也是在我和團隊反復實踐、集思廣益中,創排完成并得到了觀眾的支持和認可。
高淵:您曾說,您是保守陣營里的叛逆者,是激進陣營里的保守者。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可以體現“守正創新”的辯證關系?
尚長榮:我一直認為,戲曲人要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我們既不要拘泥于復制前輩,覺得“祖宗之法不可變”,也不要隨意解構雜交;既不要被僵化的思維困住,也不要隨波逐流地趕時髦,讓創作屈服于獵奇。
創造和創新的關鍵,是在合適的場合用合適的方式。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們排《貞觀盛事》時,大膽選擇管弦樂隊,因為大樂隊的氣魄能烘托盛世氣象,而到了排《廉吏于成龍》時,我堅持用民樂伴奏,因為民樂更貼合主角清廉的形象和作品簡樸的品相。
我從不拒絕流行的東西。2000年的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上,在《明星反串鬧新春》節目中,我按京劇花臉的唱法演唱了歌曲《愛的奉獻》。我一唱,臺下觀眾樂得直不起腰來。這就是傳統藝術與流行元素結合后,出現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這幾年跟滕俊杰導演合作,先后把《霸王別姬》《曹操與楊修》《貞觀盛事》等拍成3D全景聲京劇電影。其中,《霸王別姬》還獲得了國際3D電影最高榮譽——金盧米埃爾獎。我就是希望通過年輕人喜歡的方式,借助新技術,吸引更多觀眾去感受傳統藝術深層次的魅力。
高淵:如果從您十歲正式拜師學花臉算起,您唱花臉已經整整七十年了。很多人認為您結合了金少山、郝壽臣、侯喜瑞等名家的藝術特色,而且有很多創新,您是否該稱“尚派花臉”了?
尚長榮:我一直說我永遠不稱派,永遠不敢稱派,也不能稱派。但如果一定要我說屬于什么派,我說我是“尚派”,但不是“尚長榮派”,而是“尚小云派”。
高淵:您是花臉,表演以大氣粗獷為要;您父親是青衣,表演以柔美嬌艷為美。您為何自稱“尚小云派”?
尚長榮:這又得說到上海。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上海參加一個戲曲座談會,會上有人說,在尚長榮身上,隱約可見尚小云的藝術風格。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后來有意識地對自己和父親的表演風格進行比較。我慢慢發現,我在藝術上很像父親,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演出經驗的積累,無論是藝術理念還是表演風格,我們都越靠越近。
我學戲有一點與眾不同,除了跟老師學,回到家里還要過父親這一關。雖然我跟父親隔著行,但父親可以說生旦凈丑行行精通。他小時候初學戲是學老生,后來改學武生,老師說他扮相俊美、嗓音嬌脆,建議他改學旦角。
對人物進行熱處理,表演像一團火,是我父親和其他旦角演員的最大區別。而自打我學花臉那天起,父親就不斷跟我說,花臉一定要有虎氣,上臺千萬不能蔫。所以,我所追求的表演風格始終是大氣磅礴、雄渾陽剛。就此而言,我跟父親在藝術上是一脈相承,我說我是“尚小云派花臉”,并不為過。
高淵:而這團火、這股虎氣,您不僅用在花臉的唱與做上,更用在了京劇的守正創新中?
尚長榮:戲曲不僅要帶給觀眾藝術享受,還應觀照現實,并有啟迪作用。新時期,我們在把握傳統戲曲的深邃底蘊,用活傳統戲曲的深厚技巧,保持每個劇種的不同風格、個性及美學內涵的前提下,還應融入這個時代,適應觀眾新的文化需求。
戲曲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好聽、好看、觸動人情世情,從題材選擇到舞臺修辭,無不圍繞著這點。我們要有信心激活傳統,捍衛劇種本體的生命力。傳統是可以在表演中被激活的,傳統的敘事、傳統的舞臺元素,可以在重組轉化后,溝通當代觀眾的精神世界。這就是文化自信,也是創作的精神力量。
責任編輯:楊博 沈彤
新聞熱線:021-6131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