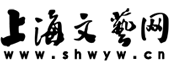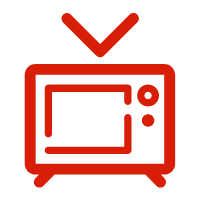“我家在上海,一代又一代……”琵琶聲起,吳儂軟語。剛過去不久的2020年年末,由上海市百靈鳥藝術團等單位主辦,上海市民文化節秘書處、上海音樂家協會、上海民間文藝家協會、上海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上海市群眾藝術館指導的《“上海謠”都市的鄉愁——侯小聲作品音樂會》,在寶山區智慧灣創意產業園依弘劇場上演。滑稽戲演員顧竹君、評彈演員陸錦花、民歌歌手袁金鳳和崔葉華4人,在同一個舞臺上分別以說唱風格、評彈風格、民族風格和鄧氏風格演繹起同一首歌曲——《上海謠》。
這首飽含著糯糯申城韻味的《上海謠》,是侯小聲創作于2011年,至今也有10個年頭了。由原上海朱家角鎮文體中心主任李振東作詞、徐蓉(戲曲風格)、林寶(流行風格)、袁金風(民族風格)三位老師首唱的一首上海民歌。“短短的民謠唱出了上海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唱出了濃濃的上海味,使人們在歌聲里品咂出一份難忘的都市鄉愁。”新年初始,當筆者在上海文藝會堂咖啡廳采訪侯小聲老師時,他深情地道出了創作這首上海民謠時的都市情結。
愛唱“上海謠”,歪打正著跨入上音學府
出生于1947年的侯小聲,在浙江嘉興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學生時代,在祖母和父親的影響,從小就愛唱歌。祖母會唱好多江南小調和山歌,侯小聲依偎在祖母的身傍,也學會了好多江南民謠。父親侯家聲年輕時就讀于福建音樂專科學校,畢業后回到浙江任中學音樂老師,解放后曾擔任嘉興市民主促進會主委,被譽為“嘉興民進的一面旗幟”,一輩子從事音樂教育,是一位樂器演奏方面的多面手,曾在杭州、金華等地,舉辦過多場“二胡獨奏音樂會”,也喜愛寫寫田山歌,曾創作了《南湖頌》《送糧》等江南民歌作品,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還出版過嘉善田歌組歌聯唱《黃浦太湖結成親》密紋唱片。
深受祖母和父親的熏陶,侯小聲繼承了老一輩的音樂衣缽,在學生時代就顯現出他在音樂演唱和創作上的天賦。在嘉興中學求學時,他擔任學生會的文娛部長,寫過小歌劇與同學們一起演出。因對音樂的酷愛,夢想就是做一名歌唱家。
1965年,中學畢業后的侯小聲,一個人從嘉善跑到申城報考“上海音樂學院”,在面試時,他演唱了一首江南民歌《長工苦》和歌劇《江姐》中藍洪順的一段唱腔,面試老師聽后雖然稱贊了他唱得不錯,可最終給他的評語是“你還是業余唱唱蠻好”。侯小聲心不甘,與另一位同學連夜趕往南京報考“南京藝術學校”,但吃了“閉門羹”。此時已鐵了心要投身音樂事業的侯小聲,又立馬重新回到上海音樂學院,參加“作曲類”的考試。令侯小聲意想不到的是:“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行”。他自己作了充分準備報考的“聲樂類”,未能天隨人愿。而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參加“作曲類”的考試,卻獲得了“金榜題名”,真可謂是歪打正著,他總算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高高興興地踏進了上海音樂學院的大門。
進入“上音”后,王品素老師知道侯小聲是一個喜歡唱歌的人,就問他:“還想唱歌嗎?”“想!不唱山歌心不爽。”這可是侯小聲報考“上音”的初衷噢!所以,他選擇的副課就是“聲樂課”。誰知正正規規的求學不到半年,“文革”就開始了,正常的上課秩序被打亂了,只能靠自己刻苦去自學和虛心向老師求教。雖然課堂里學得少了,但因經常參加社會實踐活動,特別是到農村去宣傳、采風,汲取社會的養分時間多了,與自己喜歡的山歌、小調等一些江南民歌的接觸機會也就增多了,再加上老院長賀綠汀在教學管理中對民歌的重視,使侯小聲對江南民歌的學習和采集興致更濃厚。所謂“東方不亮西方亮”,幾年下來,侯小聲在“上音”的正規課堂和課程中沒有學到多少,卻在社會的“大課堂”里收獲頗豐。他進“上音”后所創作的第一首音樂作品,就是帶有江南民歌色彩、用滬語演唱的《小扁擔》,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刊用。
迷戀“上海謠”,轉崗多處不減鉆研激情
因“文革”的原因,侯小聲這屆學生一直到1973年才正式從上海音樂學院畢業,在畢業分配前,老師問他今后想做些什么?侯小聲回答說喜歡搞搞民間音樂,學校就將他分配到上海評彈團,也算是滿足了他“搞搞民間音樂”的愿望。這個初對評彈一竅不通的人在評彈團擔任起音樂老師,并足足在那里待了5年。在這期間,侯小聲對江南民歌的情結并沒有減退,在評彈團外出演出中,他也經常登臺穿插演唱一些江南民歌,從觀眾的熱烈掌聲中他感覺到老百姓對江南民歌的喜愛程度。在評彈團的5年期間,從音樂創作上來說,侯小聲并沒有什么較大的建樹,但“評彈”作為江南的主要劇種之一,他從聽不懂到喜歡聽,接觸久了感到評彈音樂也是很迷人的。他不僅從評彈中學會了一口標準的“蘇州話”,而且評彈音樂對他日后的民歌創作,其影響力也是很深刻的。
1978年侯小聲轉調到上海市群眾藝術館擔任副館長,主要工作就是負責中國民間歌曲集成(上海卷)的編輯工作,他和老師鄒群等一些同事除了扛著老式、笨重的601型錄音機到寶山、金山等十個郊縣乃至他的老家浙江平湖的村戶、田頭去采風、錄音外,整天就“窩”在長樂路788號(原周信芳住處)內記錄、整理上海民歌。反反復復地聽錄音,一遍遍地校對修訂,雖然工作很枯燥,幾年下來收獲卻也不小,對上海民歌的了解有了很厚重的積淀,為自己的民歌創作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他先后在復刊后的《上海歌聲》雜志上發表了《幸福不從夢中來》《比不過》等滬語歌曲。在1986年“華東六省一市民歌匯演”上,他奉獻了取材于浦南小山歌的農村風格男聲獨唱曲《田螺姑娘等勿來》。?侯小聲深情地對筆者說:調入上海市群眾藝術館工作,是他對上海民歌,從喜愛發展到鐘情,從演唱轉入到收集和創作,是他這一生音樂創作之路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之后,侯小聲又先后轉崗到上海聲像讀物出版社任編錄部副主任、閘北區文化局副局長兼閘北區文化館館長、普陀區非遺保護中心主任等。但無論轉崗到何處工作,對上海民歌的挖掘、整理、傳承、發展這一情結,始終緊緊地拴系在他的心頭。在1994年上海電視臺推出的“戲歌大賽”活動中,他創作了多首江南方言的戲歌參賽,其中評彈歌曲《玉蘭樹下迎客來》(徐檬丹、薛錫祥作詞),由熟悉評彈的著名歌唱家程桂蘭演唱,獲得了大賽的金獎,并在1996年中央電視臺舉辦的“公安部春節聯歡晚會”節目中播出。另一首滬語歌曲《老上海尋不到自家門》(薛錫祥作詞),由著名滬劇演員孫徐春、茅善玉演唱,獲得了大賽的銀獎。從此,侯小聲的音樂創作之路,也逐漸以上海民歌為主要方向而努力前行。
傳承“上海謠”,精心創作田歌唱響舞臺
從1991年6月在上海音樂廳舉辦的《美麗的花環——侯小聲作品音樂會》,到去年底的《“上海謠”都市的鄉愁——侯小聲作品音樂會》,這兩場音樂會之間的距離就跨越了三十年。再以兩場音樂會的演出曲目對比,前者是將滬語歌曲穿插在其中演出,而后者卻是以滬語歌為整臺演出的主線一穿到底。由此可見,在這三十年的春夏秋冬里,侯小聲對“上海謠”孜孜不倦的挖掘和輸出,是那樣的勤奮和執著。特別是2007年后,上海田歌被列入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名錄,一生情系“上海謠”的侯小聲,其喜悅的心情是一般人難以體會的,他作為上海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的特聘專家,對上海民歌的宣傳和推廣更是熱情高漲、鐘愛有加,全身心地為上海民歌的發揚和光大奔走呼號,有例為證:
2012年10月22日晚,在上海市郊青浦朱家角鎮,侯小聲將一臺帶著鄉村泥土芳香、和著民歌旋律,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田山歌作為主要元素而幻化出的四幕田歌音樂劇《角里人家》,奉獻給第十四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這臺將田歌這壺傳統的芳香“陳酒”,納入到新時代的音樂劇“新瓶”內,可謂別具一格,成為上海群眾文化活動中脫穎而出的創新節目,博得了觀眾和專家們的掌聲一片。
“黃梅上岸望爺娘,閑七八月養后生。哥是秧苗妹是泥,角里人家土里長。”田歌音樂劇《角里人家》是以1953年青浦田歌唱到北京為背景、以一段曲折有趣的鄉村愛情為題材——田歌王子根生和音樂老師葉茂因唱田歌結緣,歷經曲折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故事。在創作這臺音樂劇時,侯小聲是煞費苦心,他以音樂劇的表現手法,為每個角色設計了專有的主題曲調。在演出中,音樂剛起角色還未出場,觀眾們就知道誰要登場了。90分鐘的《角里人家》,是清一色的滬語唱段,特別是在第四幕的第三場,侯小聲用了整整10分鐘時間,在沒有添加任何現代音樂佐料的情況下,以交響樂方式呈現原汁原味的田歌音樂而令人驚嘆。整臺音樂劇把蓮花咹咹調、大樂調、倒十郎等數十種江南小調以及搖快船、江南船拳、阿婆茶、粽子舞、走三橋……等江南農耕文化融為一體,讓觀眾們聽得有滋有味、看得眼花繚亂,充分領略了江南民歌的獨特風韻。為了能正確把握好滬語田歌的原汁原味,侯小聲走訪了青浦縣趙巷鎮的國家級田歌傳承人——九旬老漢王雪余、練塘鎮南王浜村的尤永芳、黃順芳等一批老田歌手,聽他們唱,跟他們嘮,深層次地去領悟滬語田歌的音樂精髓。?
除此之外,侯小聲還先后用滬語曲調為“上海朱家角旅游節”創作了反映農耕文化的系列品牌節目《插秧天》《耕耘天》《割稻天》《臘月天》(俗稱農四天);為浦東北蔡鎮創作了以描繪浦東鄉村婚嫁文化為題材的《三說媒》《三催轎》《三過橋》《三拜堂》四個章節的情景劇《嫁女歌》;還再現了黃浦江畔碼頭工人在實現機械化操作前的辛苦勞作場面的情景劇《上海聲音?碼頭號子》和兒童音樂短劇《碼頭尋夢》及男聲串燒表演唱《遠東吶喊》,這些節目,先后在世博園區、“上海之春”舞臺乃至聯合國全球藝術家大會傳播。
情系“上海謠”,發揚光大一生有緣執守
說起民歌,人們想到的就是那粗獷豪放、健朗悠揚的西北民歌,如“信天游”“花兒”等,還有就是電影《劉三姐》《阿詩瑪》中多情委婉、韻味優美的少數民族山歌……而說起地方語言歌,人們又總會想到的是南方粵語歌,而上海民謠、滬語歌曲,卻往往被人們忽略或遺忘。因為在人們的記憶中,上海十里洋場、西裝旗袍,會有什么廣為流傳的民間歌曲可言?其實不然!上海還是涌現出很多有影響的民歌,有些民歌還是十分流傳的。比如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天涯歌女》《四季歌》,五六十年代的《啥人養活仔啥人》《六樣機》《社員挑河泥》以及滬劇曲牌《紫竹調》等,都充滿了江南人文地域、風土人情所賦予它的清麗柔婉、細膩平樸的音樂特性。用侯小聲的話說:“上海民謠老靈額。”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那伴著黃浦江水流淌了一個多世紀的上海港“碼頭號子”,是上海碼頭工人創作和傳唱的勞動者之歌,自上海港開埠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一直傳唱于沿江數十里碼頭上貨場的裝卸、抬扛、推拉等勞動場地。在1934年聶耳創作的舞臺劇《揚子江風暴》中就有以“碼頭號子”為基調的《碼頭工人歌》。因為上海的碼頭工人來自全國各地,因此,上海的“碼頭號子”包含著各地方言的語調、節奏和傳統民歌的唱腔,具有典型的海派特征。根據勞動方式的不同,上海的“碼頭號子”還被細分為“搭肩號子”“杠棒號子”“堆裝號子”等六大類,號式繁多、唱腔豐富,其中以“蘇北號子”和“湖北號子”最具有代表性和普及性。
解放后,隨著現代工業文明的進程、港口生產機械化程度的提高,特別是改革開放后港口運輸企業的逐步遷移,黃浦江兩岸被建設成寬暢秀麗的濱江大道,“碼頭號子”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而銷聲匿跡,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
所以說,“碼頭號子”是上海典型的傳統民歌之一,保護和傳承“碼頭號子”,其實就是為了保存工業文化、海派文化,留住城市的記憶。作為上海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的特聘專家,侯小聲早就關注和參與“碼頭號子”的發掘、整理工作,他與同事們已將近百首“上海港碼頭號子”收錄進《上海民歌集成》。但是侯小聲認為:“碼頭號子”雖然大多是“吭呦啰”“嗨唷嗨”之類的虛詞,但音樂風格猶為鮮明,充滿了上海港口音樂的特色元素,是上海開埠以來最經典的民間音樂之一。然而,在目前反映上海文化的影視、歌曲和舞臺作品中,卻很難聽到這種音樂。如果“碼頭號子”能經常被運用到反映上海文化的各種文藝作品中去,它被人們認識和了解的機會與價值,肯定會比僅被作為“非遺”保存起來要多得多、好得多。如果社會各方都能意識到保護“碼頭號子”的重要性,應該還可以挖掘更多的“碼頭號子”曲目。
目前,侯小聲已著手準備再創作一臺大型音樂劇,將上海的“碼頭號子”激情高亢地展現在舞臺上。但目前創作力量比較單薄,他盼望有更多的創作者能加入到這個隊伍中來,共同攜手再呈現出一臺繽紛精彩的“上海謠”。
鑒于侯小聲對上海民歌、滬語歌曲的挖掘、保護、傳承和發展所作出的貢獻,人們戲稱:《上海謠》就是侯小聲,侯小聲就是《上海謠》。而侯小聲卻說:“不必記得我的名字,只愿大家記得《上海謠》,更愿諸君記得上海——我們的家園有著許許多多好聽的民歌……”。
責任編輯:楊博 沈彤
新聞熱線:021-61318509